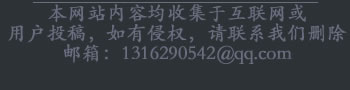首页 > 最新信息 / 正文

皮埃尔·马南1949年出生于法国南方城市图鲁斯,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哲学系,曾经在法兰西学院担任雷蒙·阿隆的助手,参与创办法国著名思想刊物《评论》(Commentaire)并曾担任主编,现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在深入阐释西方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借助这一阐释来辨析现代西方特别是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如现代国家的特征、现代民主的本质、自由主义的发生与演化、欧盟建构的政治哲学等等。
今天的推送摘选自马南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新民说新书《城邦变形计》,该书对荷马以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政治历史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创造的深入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体的分类中,将三类好政体——王制(kingship)、贵族制(aristocracy)、共和制(polity)——与它们的三类“变体”相对,那是三类坏政体:僭主制(tyranny)、寡头制(oligarchy)、民主制(democracy)。实际上,如亚里士多德接着所解释的,大多数当时的城邦都是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或者拼接,因为,如我们清楚认识到的,城邦由于数人与多人之间的冲突主张而动荡不已。没有明智的调停,数人与多人之间的战争造就了僭主。因此,理解政治生活最平常且最有用的概念是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的概念。

关于王制,亚里士多德说了些什么呢?它看起来在他描绘的图景中占据了较大的位置,其中,他辨识出不少于五种形式的王制:
1.拉哥尼亚王制,属于世袭的军事指挥终身制。
2.某些野蛮民族的王制,人们可以说,那实际上是传统的僭主制。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因为野蛮人在其禀性上比希腊人更具奴性(那些在亚洲的野蛮人比在欧洲的野蛮人更具奴性),因此,他们忍受主子的统治而不起来反叛”。这是一种世袭僭主制,由于涉入其中的人群的禀性,对这种制度本身是没有经验的。
3.那些被称为艾修尼德人(aisymnetès)的王制:这些人是由敌对党派为了结束内部纷争而指派的。他们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不用向任何人负责。亚里士多德将此类王制形容为公举僭主制。
4.“英雄时代”的王制,同时包括了号令臣属、世袭以及遵照法律。
5.一个单独之人是所有事物统治者的王制——pantônkurios(全权君主)——如同每个人和每个城邦都是其共同事务的统治者。国王在王国中类似于父亲或主人在家庭中。
此一分类颇具误导性,竟然有两类“王制”实际上毋宁是某种特别的僭主制。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立刻补充说,“根本上,只有两类王制必须从详研究……其他的大多介于这两类之间”。这两类极端的王制支撑着君王制度(royal regimes)的拱,它们是什么呢?其一是拉哥尼亚王制,另一个是绝对王制(absolute kingship)。
第一类严格地说并非王制,因为它严格地说不是一类政体,毋宁只是一项立法规定:stratègos(统帅)职位在所有政体中都可存在。于是,亚里士多德说,它可以搁置不论。
另一种,对立的一种——王制,相反是真正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讨论得最详尽,其阐释明显疑问重重。它将两个尤其令人为难且棘手的问题搅在了一起。
一个问题是探询城邦如何面对那德性超越其他所有人的个体之人;另一个问题是探询是否最好法律的统治就比最好之人的统治更值得选择。

关于第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似乎毫不含糊:绝对权力应该赋予如此一个优越之人——或者优越世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直接将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联结起来,将政治等级(“谁统治?”)与自然等级连接起来,而且赋予绝对主权以本体论的基础,此一论断影响深远;在后来欧洲“君主制的”历史上,它被演绎出千般姿态。由于它似乎脱离了任何政治背景,也能在任何背景中去主张,此论断在一种完全脱离希腊背景的政治和神学背景中更容易得到严肃对待。但是,这般严肃地对待此一论断恰当吗?提到了宙斯就已经暗示了此论断的修辞性质。
为了将辩诘的术语陈述得更恰当,让我们考察第二个问题:是否最好法律的统治比最好之人的统治更可取。我们立刻要说明,恰是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问题的事实就表明,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不满意。那么他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呢?
反对法律统治的论据,以及同样地,赞同人——更不要说最好之人即国王——的统治的论据是,法律只能订立一些普遍规则,对于具体情境则束手无策。的确如此,不过,另一方面,那些统治者随意支配之际也不可缺少此类普遍的规则。如此,没有法律人们将一事无成。法律的德性是其缺乏所有的激情,而每一个人的灵魂必然包含了激情。因此,人的统治的优越性是它能够考虑具体情境;而法律统治的优越性是它对激情的免疫。于是人们不得不将人的统治——或者最好之人的统治——与法律统治混合或者结合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依然很笼统。让我们更细致地来审视。的确,法律不能处理具体情境的细节。但是,一个人就更擅长做这些吗?当然不是。那么,该如何做呢?法律会给予执法者在此类事务上的一种特别教导,并且训练他们裁判、处理“最公正的意见”遗漏未曾裁断的事务。通过这种方式,法律借助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统治者——矫正法律的缺陷。

因此,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汇聚一处,审断、会商、判决,而判例本身都涉及具体事务”。思考此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允许我们更为自由地考察“最好之人”呈现的情形,因为,尽管公民大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个体的——相比而言,比最好之人的功绩可能逊色不少——但城邦是由许多这样的人构成的,正如许多人出资筹办的宴席胜过一人办的宴席,一众人等在许多事例上比一人的裁断更好,无论此君系何人。
这里出现了一种论证(在《政治学》的好几处都可见到)令我们吃惊,因为它不仅有着明显的民主特征,而且此一特征显得如此极端,以至于一位现代民主人士也会犹豫着不去支持,甚至会拒斥它。此“民主论证”的性质和含义需要界定。它并非教条的,譬如假定政治的公正就是由多数的意志所决定。它本质上或内在地是一政治论证,我的意思是,它不仅是一则针对政治事务的论证,而且它的要领以及可以说,它的生命都效仿了我们的政治境况。它揭示了数量的权力(powerofnumber),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复数性近乎无可阻挡的力量,这种复数性是我们政治境况的典型特征。无论一位个体之人是多么卓越——和许多现代民主人士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自然差异——他的优越性是在一个密集的人群中自我展示的。那是如下之人构成的“群”,他们无须特别的优秀,但不是没有才能或者天赋,他们共同建立了城邦,在某些方面集聚此类特性和天赋,达到这样的程度:胜过卓越之人的判断。
人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民主判断与卢梭平等主义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根据后者,不具特殊禀性之人的良知是最好的甚或是不会犯错的善恶判官。它多少可在这一谚语中找到印证或者表达,即“众人先生(Monsieur Everybody)较伏尔泰先生才智更胜一筹”。
探寻此一论证的所有衍生结论没有意义,不过,让我们留意其中一则,那与我们的关切息息相关。那个在原则上独自统治的人并非不受数量法则(law of number)或者复数之人的权力的影响:“因为实际上,君主为自己创造了诸多耳目,还有手足;那些对他们本人及其统治友善之人,他们使其成为共治者。如果他们不是朋友,他们就不会与君主的意图一致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是他及其统治的朋友,朋友是相似和平等之人,因此,如果他假定这些人应该统治,他[必然]假定那些相似和平等之人同样应该统治。”

如果数量此前的逻辑是“民主化”,那么这里则是“贵族化”。无论对王制的论证(royal argument)和对王者(the One)的论证具备什么样的抽象效力,王者的权力、王制的权力在其两项限定之下都服从复数的政治境况,一个限定是多人集聚其德性之时,在某些方面会胜过最好之人的德性,另一个限定是国王的友爱会衍伸至数人中间,这些数人会变成多个与国王平等的人。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绝对王制,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留下来的有效存在的唯一王制,最终在亚里士多德探索的希腊政治经验中,没有自己的质料(substance)。绝对王制概念之必要就在于提供数量金字塔——一人、数人和多人——的顶峰,让我们的政治境况条理化,并且让我们理解它。与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甚至贵族制和共和制不同,它并没有命名一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政体。
不过,你接着就会说,难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希腊全然忽略了王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它的名称自何而来,它又是对什么加以命名?不,希腊并没有全然忽视王制政体(kingly regime)。如果我们返回至我们开始的地方,就会看到亚里士多德提到过一种王制,我们尚没有对其加以任何评论,即第四种,“英雄时代”的王制,它同时包含着号令臣属、世袭以及遵照法律。那是希腊世界唯一实际存在的王制。让我们更为确切地思考它,尽管亚里士多德对它一带而过。
此王制属于城邦生活的开端处。它无疑以德性的优越为基础,不过却是一类非常有限的优越性,因为它是由此类小社群中卓越之人的缺乏造成的。人们忍不住要说,在人类发展的这些原始阶段,一丁点的体格或者道德禀赋——高贵的面庞、长长的头发、战斗的勇气以及和平时期的慷慨——足以使得一个人胜任王。亚里士多德暗示,某类推选,无论如何某类选择最好之人的“贵族式”程序巩固了此类原始王制:王是一位恩主,谁最能为善或者建功,就会被拥戴为王。
因此,此类有限的王制建立在一个弱小的人类联合基础上,“人丁”稀少。不过,当出现许多德性相类之人时,“他们就不再容忍[王制],而是寻求共同之物,建立共和政体”。可以看到,英雄时代的此类王制没有自身的连贯性:只要社群中的能人之辈变得多起来——这是那里存在的最自然的趋向——他们就会抛弃依靠城邦的平庸获取优势的“王”。
因此,亚里士多德用几句非常简单的话就概括了城邦的宪制历史——政体的历史。贪婪之滋长导致了寡头制。随后寡头制自身变形为僭主制。最终,僭主制为民主制铺平了道路。最后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亚里士多德暗示是因为其卑鄙的贪婪,治者群体萎缩了,由此使得大众更加强大。随着后者的反叛,民主制兴起。这一极为凝练的描述揭示了政治变革、城邦政体变革的全部动力和简明之处。这一原则是复数的竞争,数人和多人之间的竞争,数人自然而然地趋于减少,多人变得更多。在此描述中,王者,绝非政治和人类秩序三原则的构成之一,而是数人的界限。用恰当的政治术语来说,王制和僭主制只是寡头制的两类模型——其一是古代的或英雄时代的;其一是后来的、堕落时代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分析中,就没有王者政体(regime of the One)。
无论如何,“现在所发生的是城邦已经变得更为辽阔,或许除了民主制之外其他任何政体都不容易出现”。这一最终评论的涵义是什么?它似乎相当程度地限制了我们政治选择的范围。这里亚里士多屈从于必然性的威势了吗,正如现代人毫不迟疑所做的那样?我们还记得列奥·施特劳斯的论断:好政体与坏政体之间的差别是所有实践或政治区分中最根本性的,由此,就与沃格林看起来所想的相反,比宪政制度与后宪政制度之间的区别更为根本。对必然之所是的思考决不能遮蔽对善之所是的思索,对于我们来说,后者必须一直是优先的。难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不是赋予前者优越性吗?难道他不是在向我们解释说民主制——根据他的分类,这是一种坏的政体——总体上是他那时的希腊城邦唯一可适用的吗?
这会暗示,也是在说,与施特劳斯的论断相反,对于唤醒某种政体的必然性特征,古典政治科学并非那般缄默不语,这种政体如果不是完全坏的,那无论如何要比完全好的政体逊色。不管怎样,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不曾暗示对于善恶之别的丝毫轻蔑),蕴涵着对于必然性的一种不同于施特劳斯暗示的那种“作为公正惩罚的必然性”的理解。
尽管简要,亚里士多德概括了城邦的自然历史:作为一个政治形式的城邦的发展,其在数量和才赋上的成长,一种自然而然的成长,可以说必然导致某种状态:民主政体是唯一可能的政体。此政体根据民众的品质可能或好或坏,但它必然是一种多人的政体。如果民众极为腐化,它将是一类非常糟糕的民主制。亚里士多德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暗示后者可能导致——更谈不上说它必然会导致——“凯撒主义的”政体,哪怕他曾经指出,作为此类坏民主制的替代,一种僭主制可能兴起。
所有他的暗示都指向同一路径:健康或堕落的民主制是城邦的最终政体,其“自然历史”的终结,或者其历史的自然终结。这是意味深长的:民主制今时享有“政体”的属名——昔日被称为dèmokratia(民主制)的东西今日被称为politeïa(政体)。凭借此一最终政体,城邦成为其所能是之全部。其所有可能性都实现了。一种“凯撒主义”的未来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无法想象真正的革新——在这一术语的强烈意义上是没有未来的。如此一种革新会预设政治形式本身的变形,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远没有探索此等可能性,而是铺陈理由,认定其严格意义上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施特劳斯关于善之实践优越性的论点,尽管本身完全令人信服,却被他拿来与一个关于政治的理论命题或者观点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该命题认为,理解政治可归结为理解政治政体以及回答哪种政体的问题。然而,这一论点或命题是不充分的,因为,我敢说,这些可能确实是好的或坏的政体并非全部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如果它们均等地受制于一般形势(circumstances),那么它们不均等地依赖于一种形势(acircumstance),那不只是形势,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可能的政体的数量和性质,即政治形式。正如我们刚才所见,王制在城邦形式中就没有位置,除了在城邦存在的早期阶段——“王制的”(kingly)诸术语就来源于那里。因此,事情就不仅是将一类政体放在善的天平上衡量,而且是领会其与政治形式的关联。
无论人们可能多么渴望不要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缩减至或者归属在希腊经验的界限中,但我相信,如果他们这样做,是不忠实于他的路径的:抽离关于王制政体的几则极端抽象论断,以便提炼一种独立于政治形式(王制在其中有,或者如发生的,没有其位置)的王制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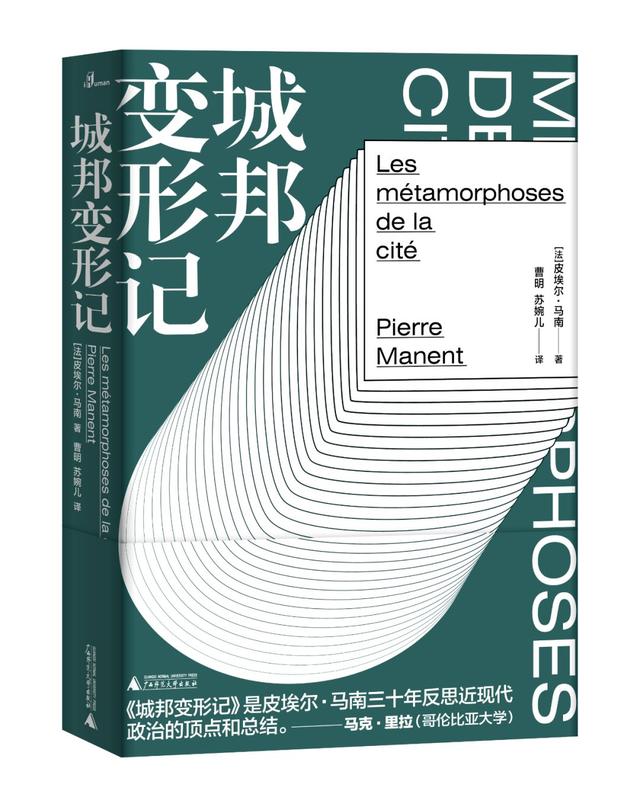
《城邦变形记》
[法]皮埃尔·马南
译者: 曹明 / 苏婉儿
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萨姆沙醒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人变成了甲虫。如果说20世纪始于这样一个时刻,即政治的死去,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如何从动物变形为政治动物,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人统治自身的最佳方式。在马南看来,西方历史便是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斗争塑造着。
点击阅读原文 进入新民说书单
超级折扣购买本书


本文作者:新民说iHuman(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700365811355222535/
声明: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仅用于个人学习、研究,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
- 搜索
-
- 06-10《雍正王朝》西山锐健营有多少兵马?雍正靠哪些部队支持才登基?
- 06-10古希腊城邦,真的容不下"国王"吗?
- 06-10此位皇帝虽有争议,但他的功绩不可抹杀
- 06-10清廷寄以厚望的江南江北大营 为何搞不过曾国藩湘军
- 06-10汉献帝本有翻盘的机会,却被此人害得,当了一辈子得傀儡皇帝
- 06-10从玩偶到斗士:中国历史上最血性的傀儡皇帝
- 06-10八阿哥胤禩为何没当皇帝?一致命环节没处理好,让康熙最担心
- 06-10古代“高考”是如何作弊与反作弊的
- 06-10美国都不敢招惹的国家,领土是中国两倍,人口还不到中国十分之一
- 06-09华容道时,诸葛亮为何要放走曹操?不放他们就完了
- 999℃云南西双版纳边防与老挝公末世之女契约师安部门达成多项共识 维护边境稳定|边防|老挝|西双版纳
- 998℃版纳植物园合作研究揭示横断山植物多样性形成机制|横断山|多样性|时间之外漫画全集物种
- 998℃南美濒危野生动物绿鬣加倍的爱情激素蜥现身居民楼 被警方捕获|南美洲|绿鬣蜥|常宗波
- 998℃世纪金源黄如论或涉行贿 曾称不能和官员cf体验黄鱼纠缠在一起|黄如论|股权|房地产_财经
- 998℃男子进女厕抢手机竟为了玩游戏 一步女性人际心理健德堂走错悔恨终身_八卦趣闻_游戏
- 998℃国考报名人造人间奇凯达第九日总人数破百万 竞争比创历史新高|2019国考|国考报名|报名人数_教育
- 998℃迎接少数民族运动会 郑州奥体中心主场9c8809馆7月中旬投用_河南
- 997℃西双版纳查获一起快递偷运疑似“老虎头骨”动物制品案|头骨|西双版ladyboy左崴崴纳|制品
- 996℃“最严调控”下4月楼你画我猜u14市全面降温 后市将继续调整|限购|调控|楼市
- 996℃驼峰机场上空的鹰:如何打通空中“最后一公里”?|腾冲|机场|秀文笔文学qq旅游
- 06-08刘禅并不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其实颇具智慧,证据有四点
- 06-08南京第三批历史建筑补充名录公示
- 06-08国民党军队派留学生去德国学习,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 06-08封神演义:闻太师征战北海,为何用了15年之久?原来跟此大神有关
- 06-08民国时期的“民主”真相之一,黄兴以“势”凌法
- 06-08影响中国历史的“五大漳州事件”
- 06-08明朝“朱三太子”晚年被康熙杀全家!崇桢子嗣被斩草除根
- 06-08清朝如何花200年的时间 把朱元璋后代养成了废人?
- 06-07吸疮之情多有谄媚之态,富甲天下却因贫困饿死,纵有金山难保周全
- 06-07董元奔吟咏历代文人‖1003不逢时:临川人王安石(1021-1086)
- 标签列表
-
- 历史 (279)
- 云南 (209)
- 西双版纳 (126)
- 万达 (110)
- 旅游 (92)
- 清朝 (90)
- 不完美妈妈 (81)
- 明朝 (76)
- 文化 (73)
- 唐朝 (66)
- 经济 (61)
- 日本 (56)
- 西双版纳州 (56)
- 政治 (53)
- 孙宏斌 (47)
- 曹操 (46)
- 三国 (45)
- 汉朝 (44)
- 融创 (43)
- 宋朝 (40)
- 刘备 (38)
- 中国历史 (38)
- 毒品 (37)
- 刘邦 (36)
- 第二次世界大战 (36)
- 朱元璋 (35)
- 王健林 (35)
- 乾隆 (34)
- 股权 (33)
- 河南 (33)
- 北宋 (32)
- 长安 (32)
- 春秋战国 (31)
- 英国 (30)
- 蒙古 (30)
- 元朝 (30)
- 房地产 (30)
- 唐太宗 (29)
- 秦始皇 (29)
- 匈奴 (28)